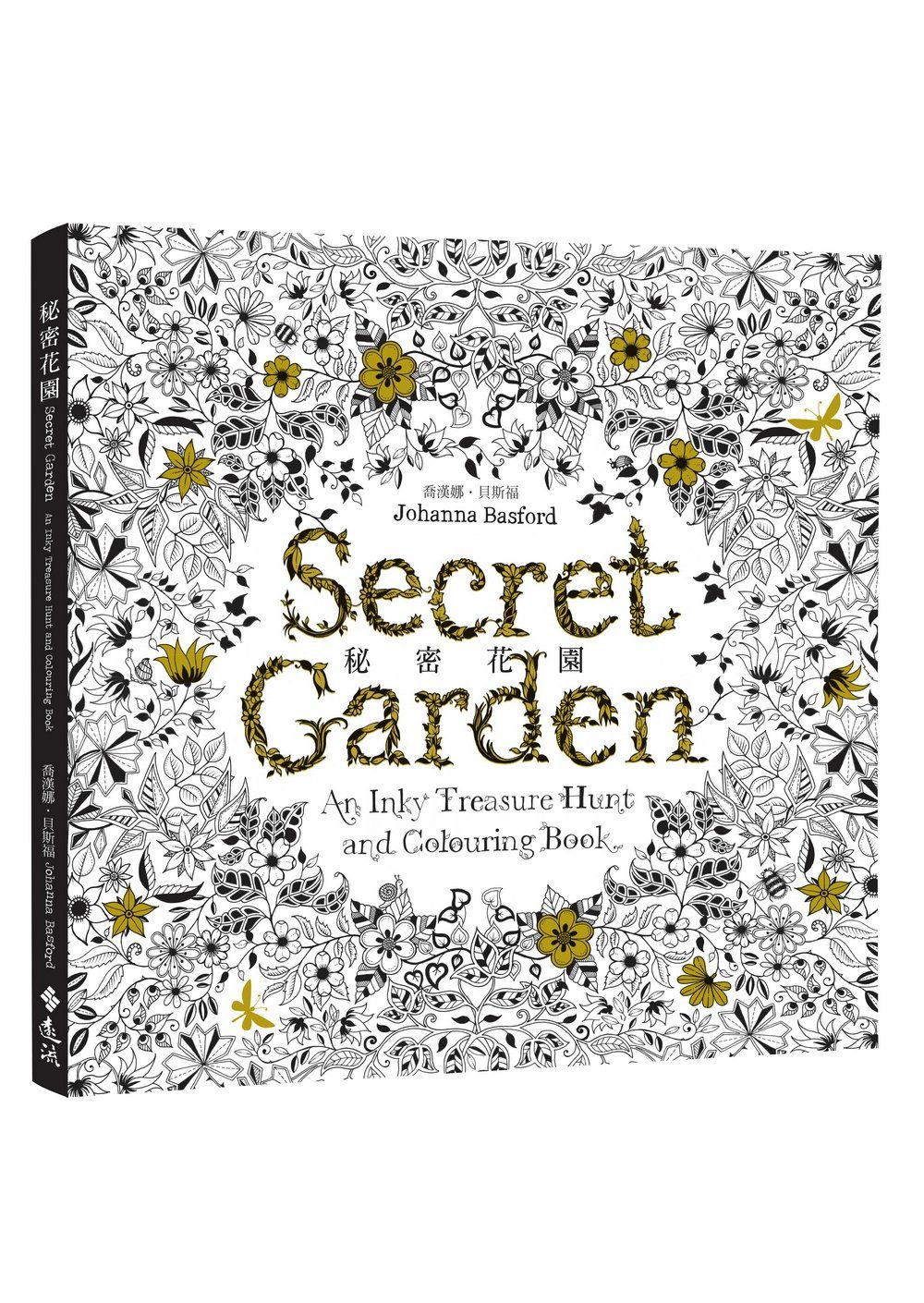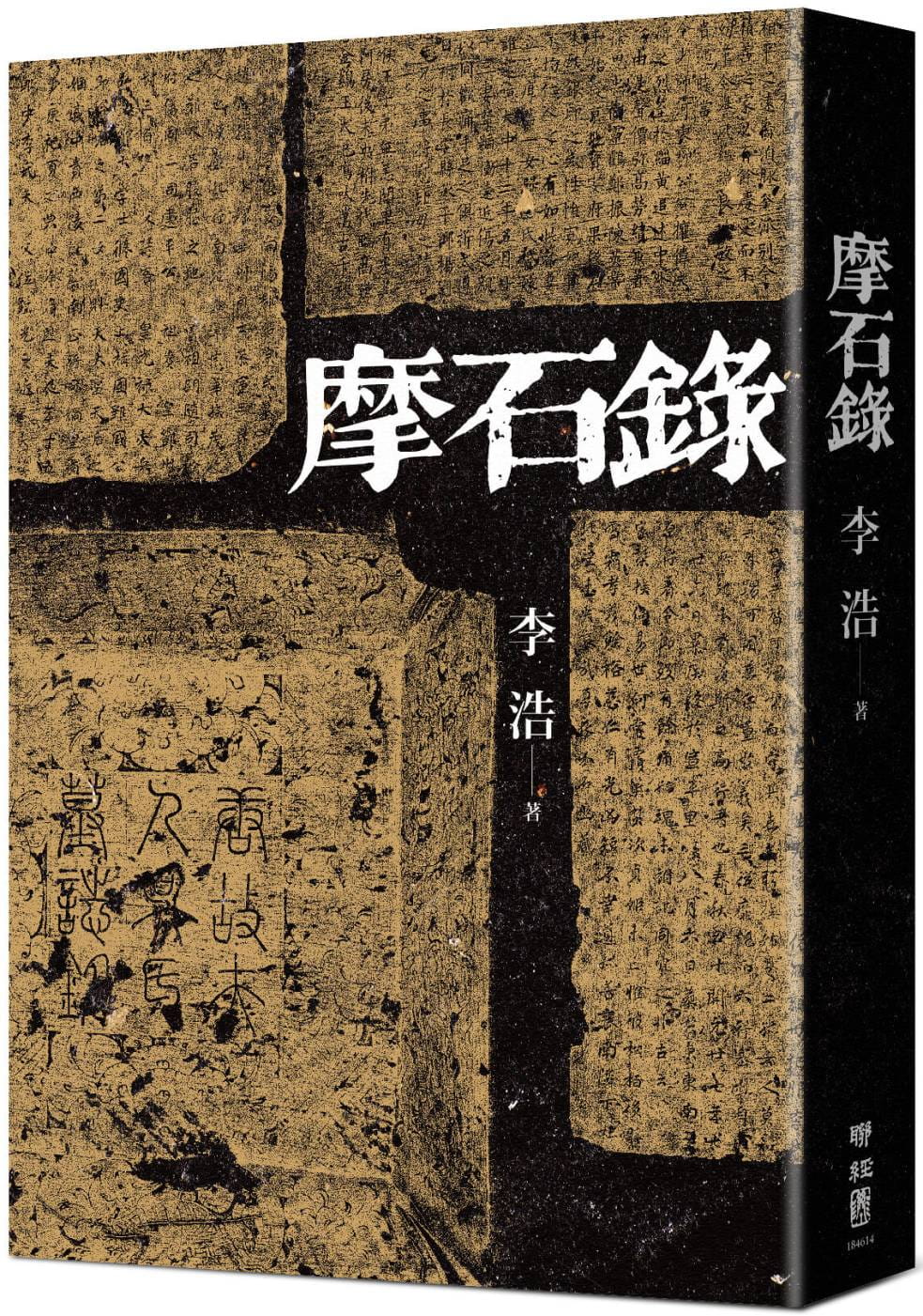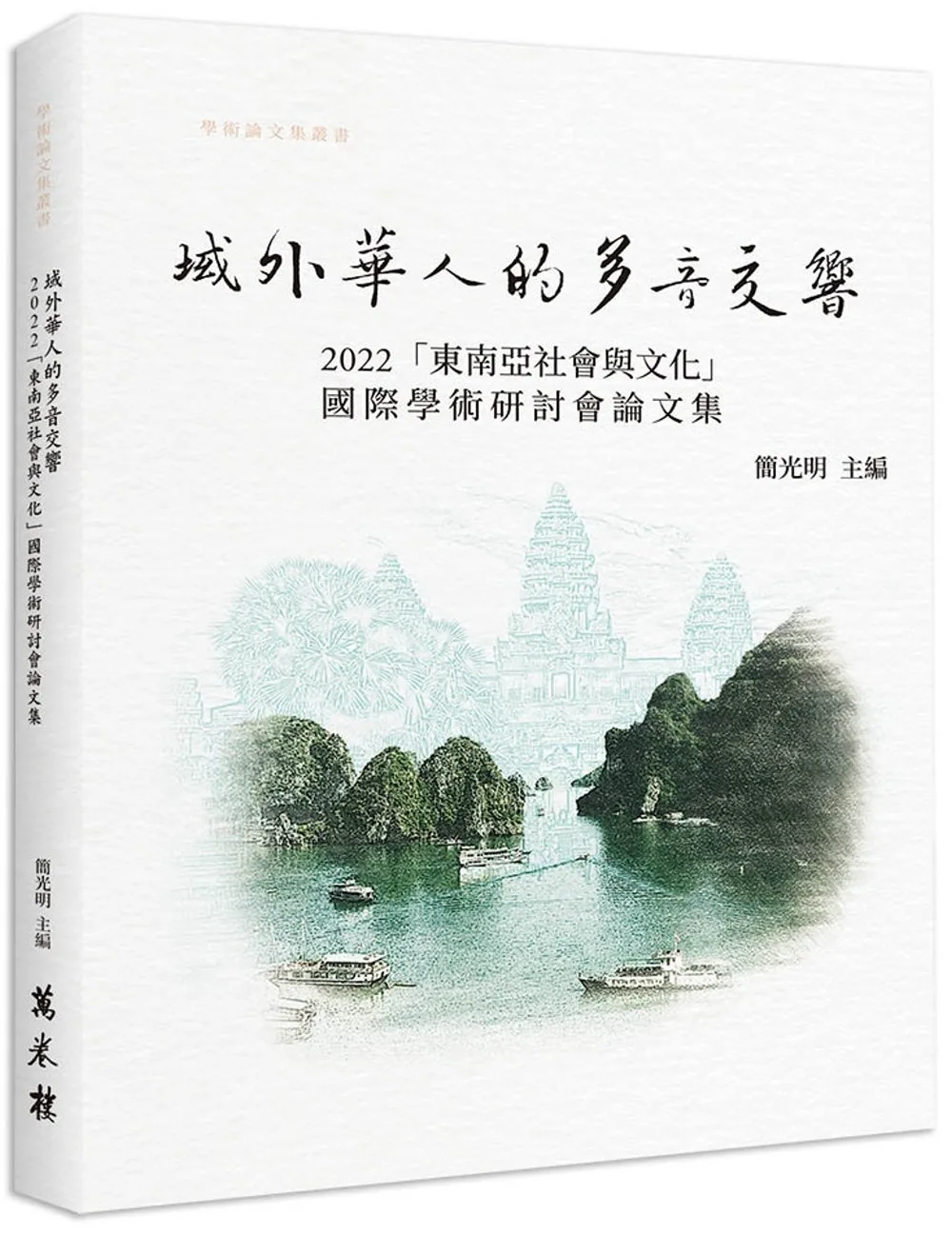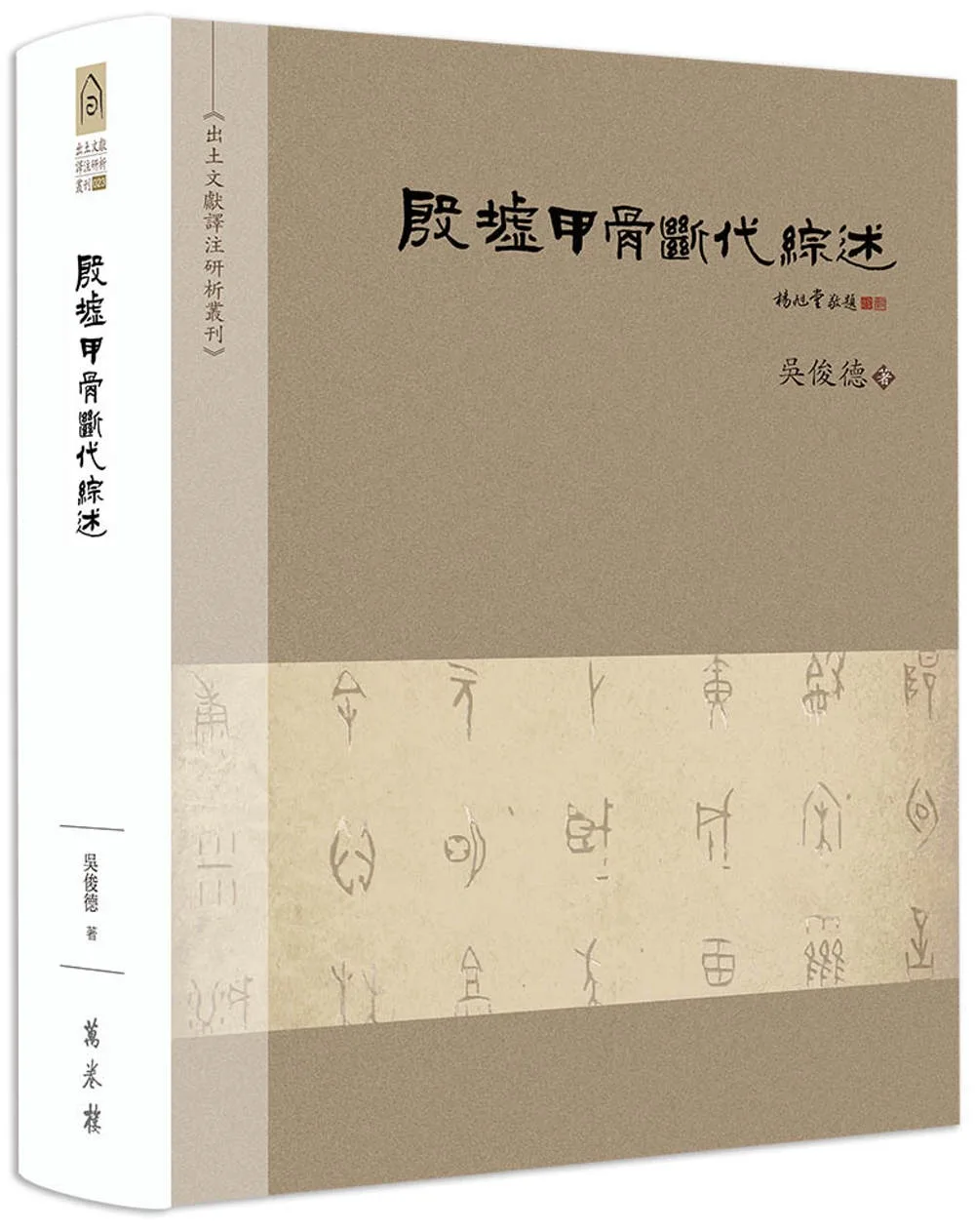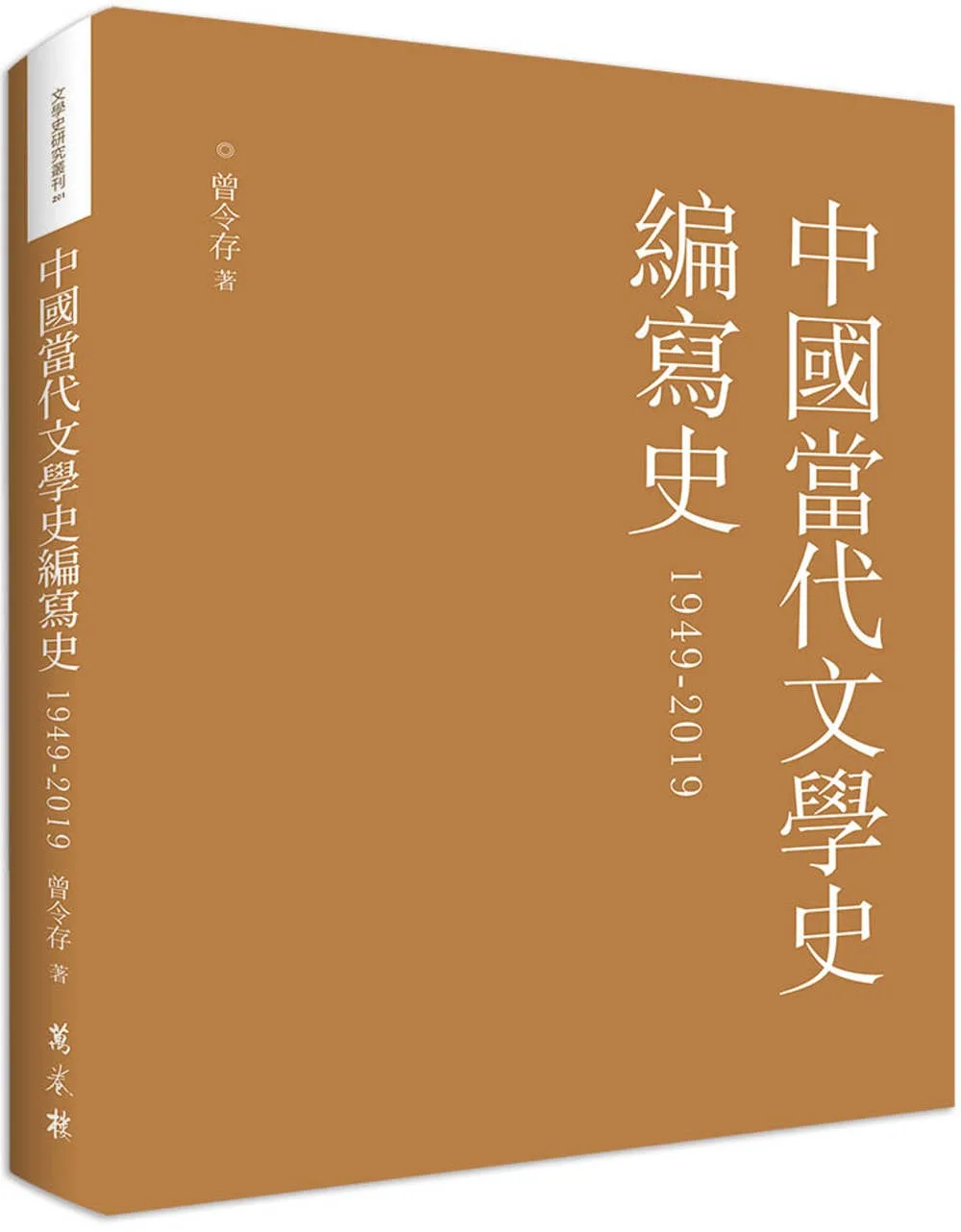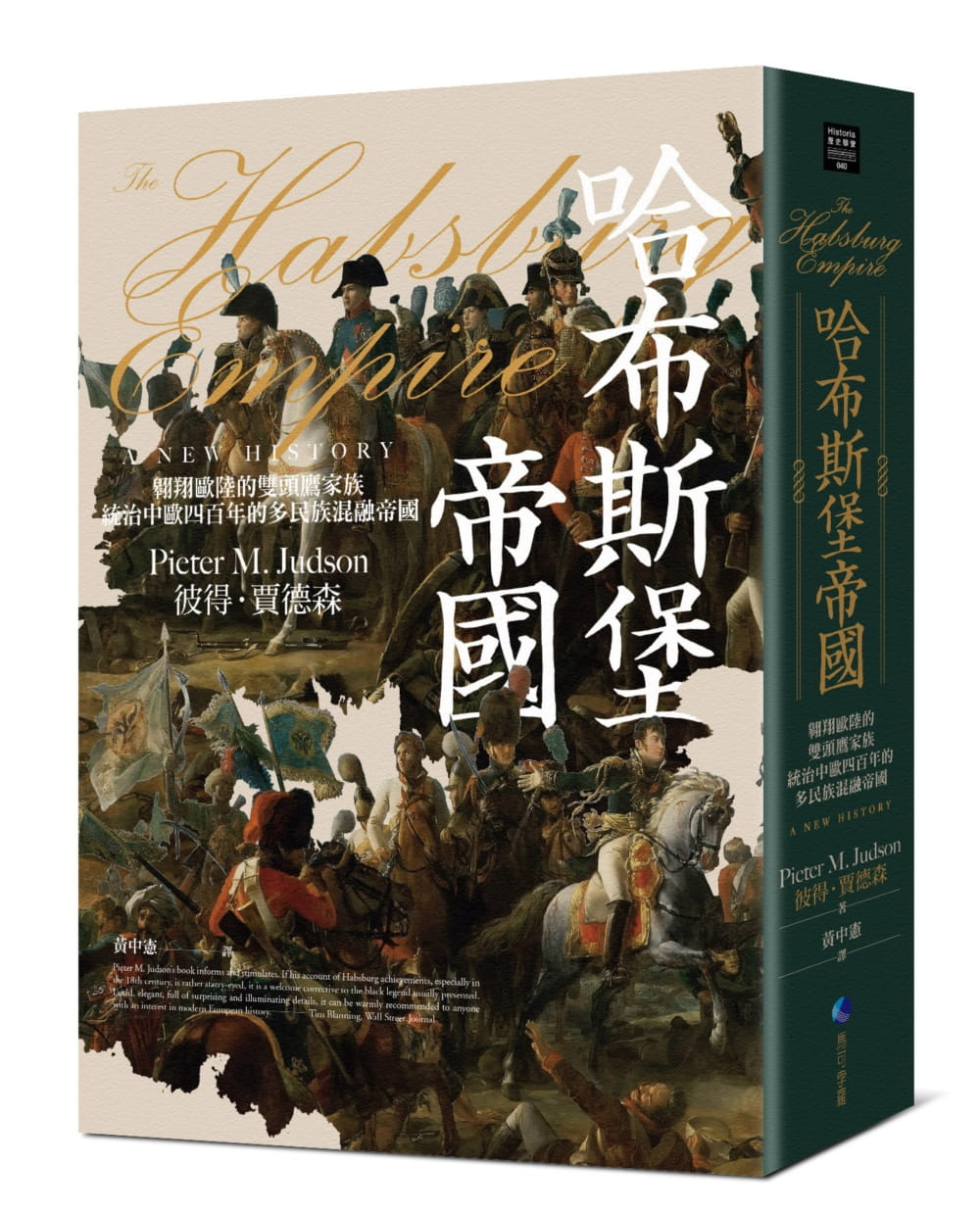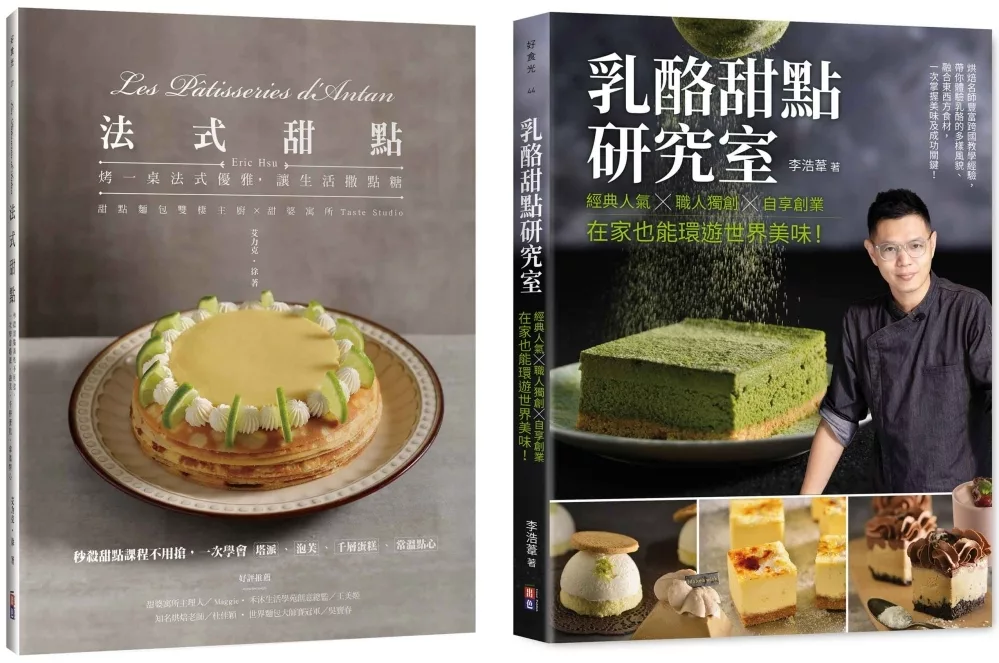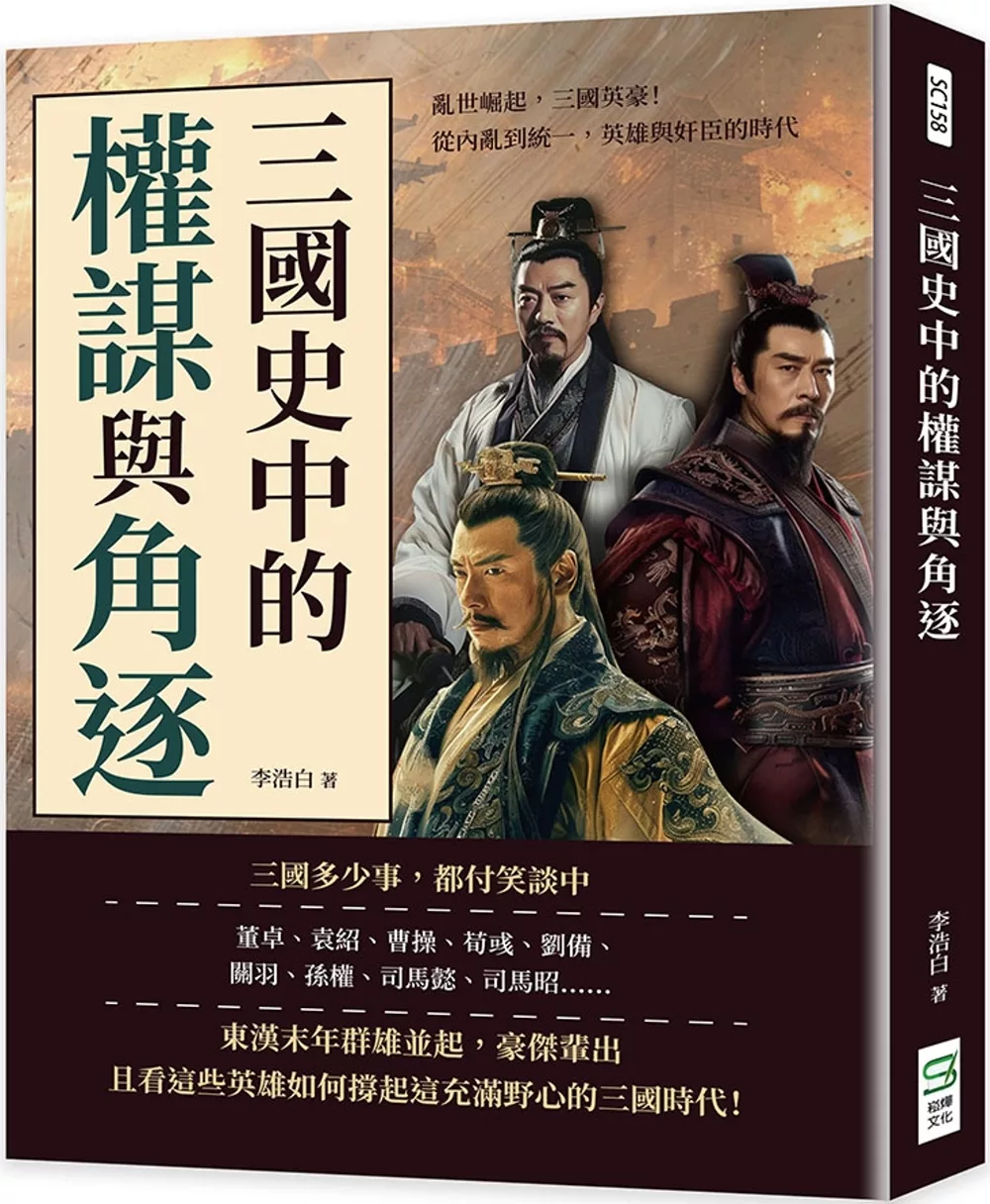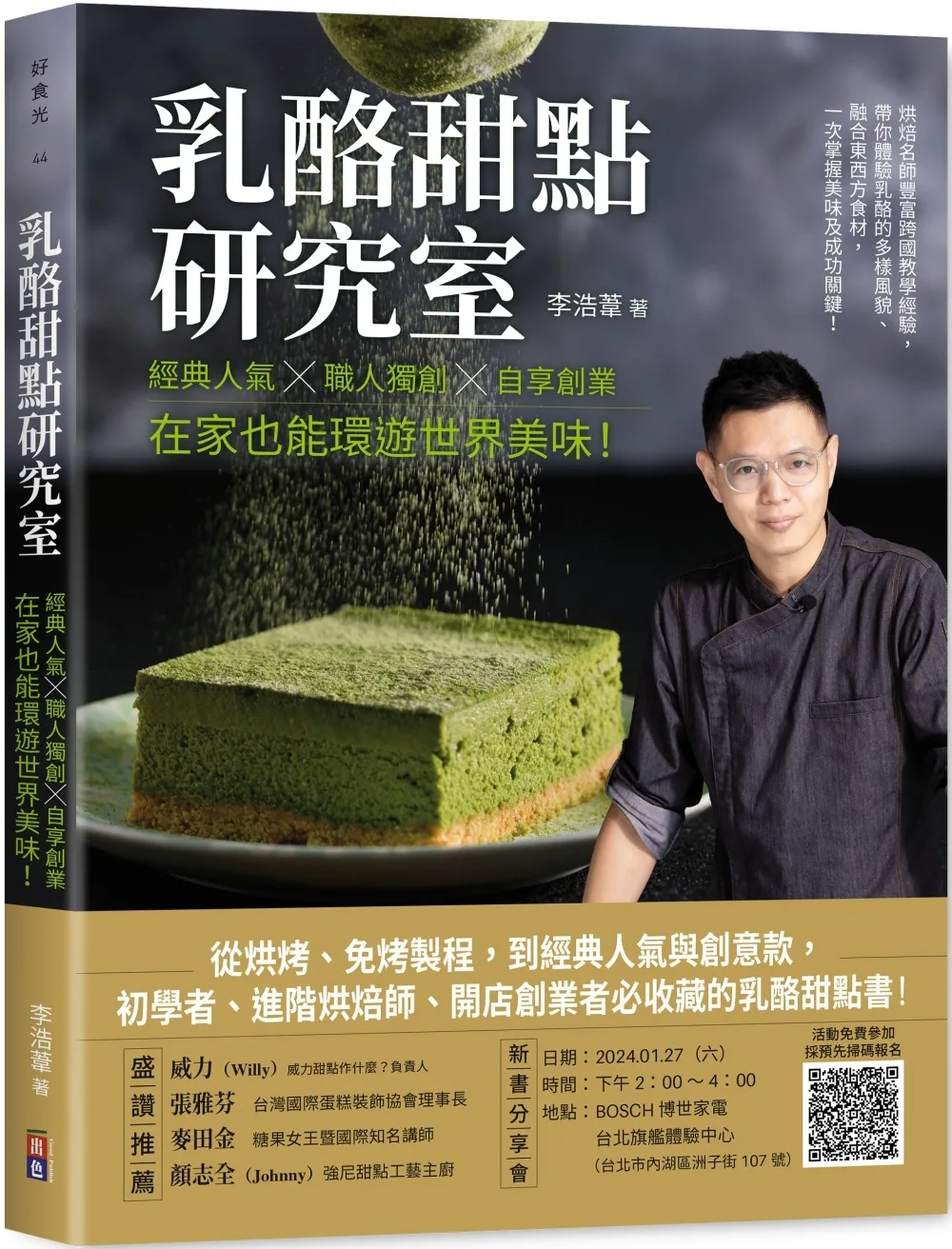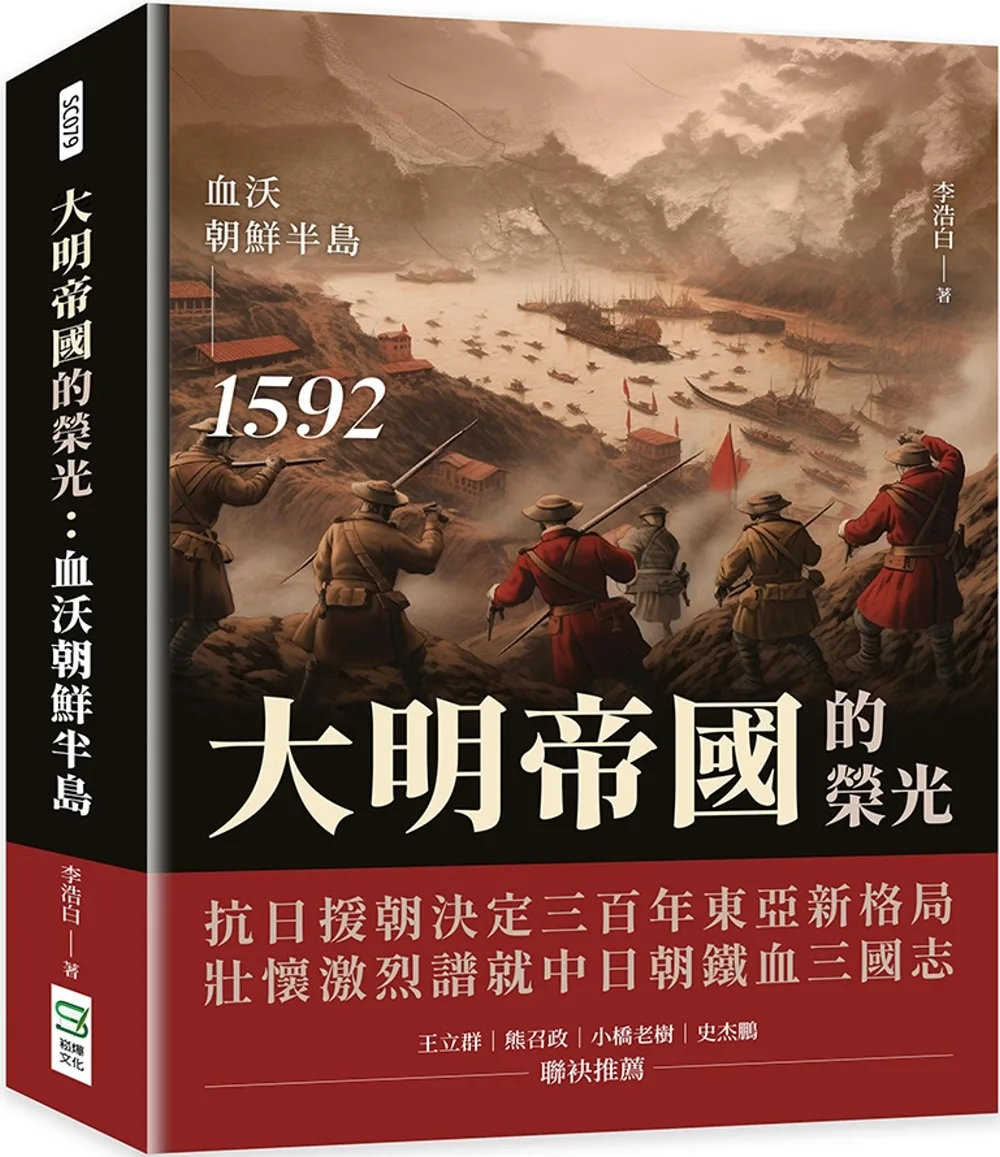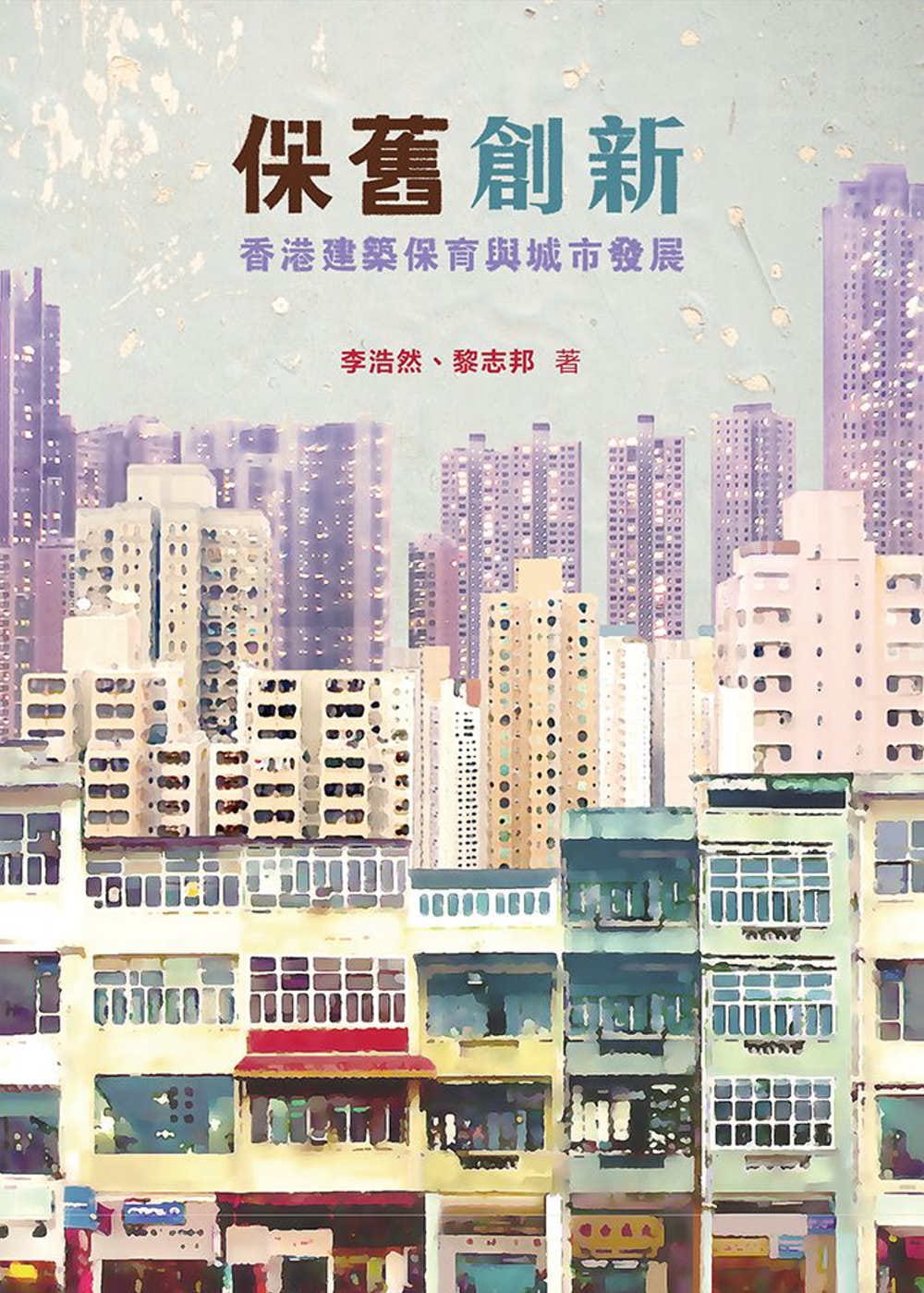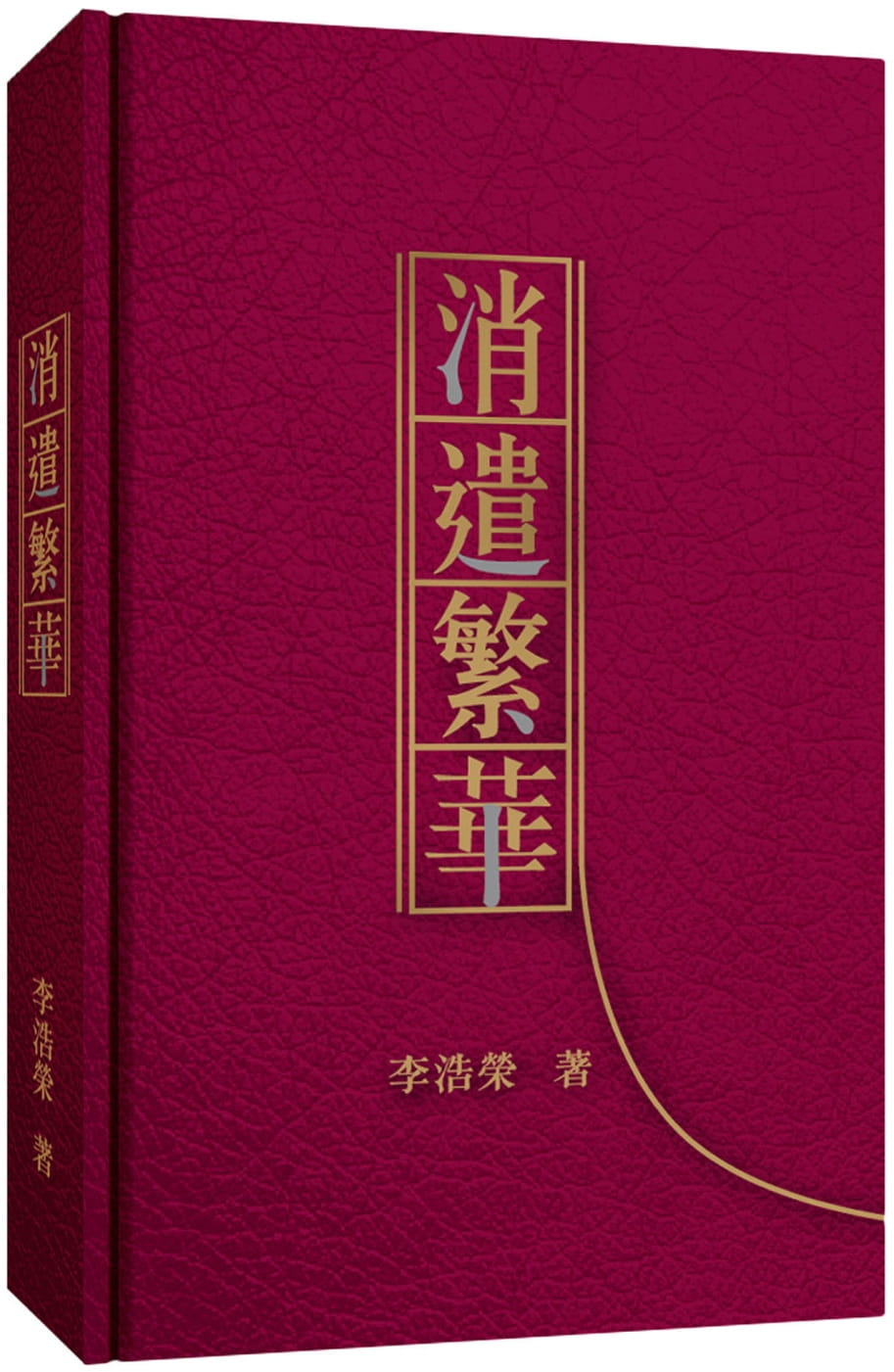序一
何寄澎(臺灣大學中文系名譽教授)
近一、二十年因著學術研究與交流的需要,我多次赴大陸著名大學訪問,也幾乎定期參加唐代學會、宋代學會的會議,以及首都師範大學、復旦大學等校舉辦的國際學術會議,因而得識大陸中文學界的諸多俊彥,其中有些亦成為君子之交的朋友,對這樣的緣分,我個人是極為珍惜的。在這些學界俊彥中,李浩先生相對沉靜而內斂,雖蒙其贈我大作若干,但彼此交談不多,算不上熟識,我從他的著作知道他研究傑出、成果豐碩,心中始終是佩服的。
去年(二○一九)秋,李先生來臺客座,因而有機會小聚,知其已撰就《摩石錄》諸稿,當下歎服不已。蓋金石之學,牽涉的知識太廣,需要的涵養太深,李先生寫來旁徵博引,井然有見,雖初試啼聲,功力已然不凡。各篇所涉課題包括:唐初樂律學,唐初政爭,士族轉型,貴族女性崇道、崇佛風氣,中唐以後石刻技藝的集團化、家族化,以及唐代與域外異族的交涉等等。各篇或補史之不足,或拓學術新視角,或揭一己獨特新見解,而莫不裨益學術,誠有足多者!閱讀上述諸篇大作時,我個人雖不能贊一辭,卻勾起久遠的記憶。蓋上個世紀八○年代初,撰寫博士論文期間,瀏覽歐陽修《集古錄跋尾》,便愛不忍釋,動念他日當就此深入研究。然因生性疏懶、專精不足,始終不敢縱身其中,僅於偷閒之時,反覆翻閱以為饜足而已。有關《集古錄》,歐公雖說:「乃撮其大要,別為錄目,因並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,以傳後學,庶益於多聞。」(〈集古錄目序〉)但我個人總覺得對自我生命、對他人生命,乃至對歷史、現實一以貫之的關切與深情,才是歐公對金石遺文懷抱無限熱情的關鍵。試看〈後漢楊震碑陰題名〉曰:「……漢隸世所難得,幸而在者,多殘滅不完,獨此碑刻劃完具,而隸法尤精妙,甚可喜也。治平元年中伏日書」,顯示的是日常生活的愛悅與適意。〈唐湖州石記〉曰:「(顏魯)公忠義之節,明若日月而堅若金石,自可以光後世、傳無窮,不待其書然後不朽」,顯示的是對顏魯公人格、氣節的崇仰。〈魏公卿上尊號表〉曰:「右〈魏公卿上尊號表〉,唐賢多傳為梁鵠書,今人或謂非鵠也,乃鍾繇書爾,未知孰是也。嗚呼!漢、魏之事,讀其書者可為之流涕也!其鉅碑偉字,其意惟恐傳之不遠也,豈以後世為可欺歟?不然,不知恥者無所不為乎?」從「未知孰是」的知性辨證到「可為之流涕」、「不知恥者無所不為乎」的感慨與凜然,顯示了歐公對歷史正變、是非的關懷。〈唐韓覃幽林思〉曰:「右〈幽林思〉,廬山林藪人韓覃撰。余為西京留守推官時,因遊嵩山得此詩,愛其辭翰皆不俗。後十餘年,始集古金石之文,發篋得之,不勝其喜。余在洛陽,凡再登嵩嶽。其始往也,與梅聖俞、楊子聰俱;其再往也,與謝希深、尹師魯、王幾道、楊子聰俱。當發篋見此詩以入集時,謝希深、楊子聰已死。其後師魯、幾道、聖俞相繼皆死。蓋遊嵩山在天聖十年,是歲改元明道,余時年二十六,距今嘉祐八年,蓋三十一年矣。遊嵩六人,獨余在爾,感物追往,不勝愴然!六月旬休日書」。字裡行間,死生無常、際遇難料、人事多變之感慨,充然在目。〈唐華岳題名〉則在人
世百端之外,尤深致嘆惋於「世變多故」,其文曰:「開元二十三年丙午,是歲天子耕籍田,肆大赦,群臣方頌太平,請封禪,蓋有唐極盛之時也。清泰二年乙未,廢帝篡立之明年也,是歲石敬塘以太原反,召契丹入自雁門,廢帝自焚於洛陽,而晉高祖入立,蓋五代極亂之時也。始終二百年間,或治或亂、或盛或衰,而往者、來者、先者、後者,雖窮達壽夭,參差不齊,而斯五百人者,卒歸於共盡也。其姓名歲月,風霜剝裂,亦或在或亡,其存者獨五千仞之山石爾。故特錄其題刻,每撫卷慨然,何異臨長川而嘆逝者也!治平元年清明後一日書」。在對人命終歸澌盡泯滅而已的感嘆中,尤透露出一己對治亂盛衰有常無常的惑與不惑。要言之,從上引諸篇《集古錄跋尾》,固可見在「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,以傳後學,庶益於多聞」的核心旨意之外,歐公更藉此表現其兼涵「小我」、「大我」的抒情詠歎,而後人正由此可窺見歐公動人的內在情懷以及筆下特殊的文字風格。我因此想到,李先生的石學研究,何妨在莊嚴的學術層面之外,漸漸添入個人浸淫此種種史料當中的所思所感、所體所悟?則或許因之別開李先生另一新勝場,亦未可知。書名《摩石錄》,我個人反覆揣想,莫非其中亦已有如歐公嗜好、把玩的心情與趣味在?則李先生對我上述的發想,何妨興乎而為此。但願不久之後能見到《摩石錄跋尾》這樣的書寫,是為盼!
?
二○二○年七月二十九日於臺北酷暑天